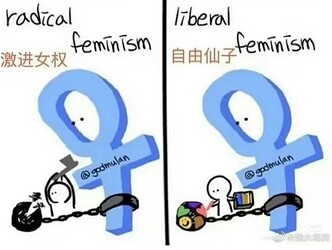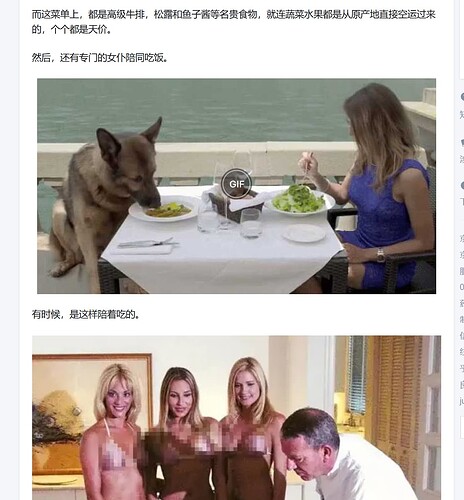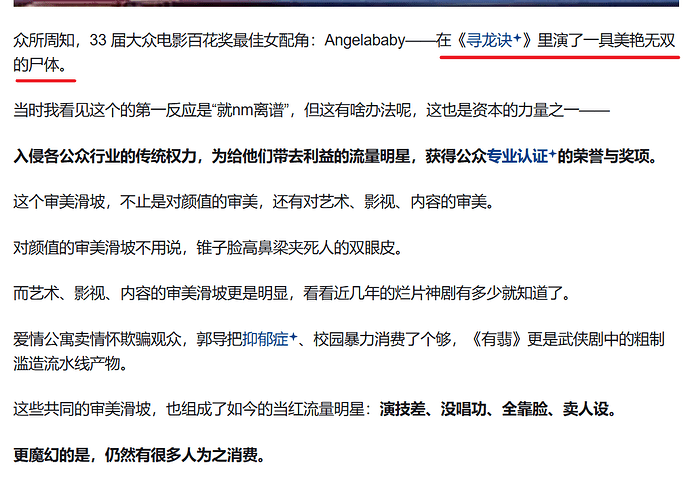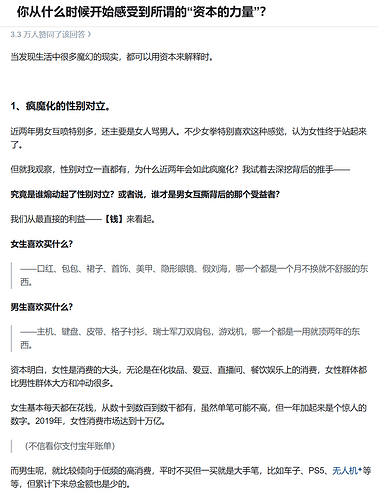从网上关于南京红姐的身份、人称代词、客户身份的争论,各方究竟在吵什么?继续讨论:
本来是打算写一篇关于跨性别与女性主义的长文的,不过看到如此典型的 not all men 言论,忍不住发出来我已经写过的片段。
与 TERF 打交道是大多数跨儿都曾经经历过的事情。相比于交谈和理解,大多数情况下无论是激进女权主义者还是跨儿,都会拒绝理解对方的思维。甚至,出于对 TERF 的厌恶与社会性厌女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一部分女性倾向跨性别者(Transfemmine)[1] 转而支持 incel 和新男权,进而仇视女权主义这一整体。
笔者认为,实际上,女性主义者应该和跨性别相互理解。这不是出于温和的尊重乃至“政治正确”的需要,而是确确实实地,出于完善理论体系的需要。顺性别者缺失的跨性别体验使得她们没有办法理解「性别认同」或者跨性别女性主义所说的「潜意识性别」[2] 的存在,对于性别的探索常常落于两个极端,即性别本质主义和性别完全社会建构理论。同样的,跨性别女性常常缺失的,作为认同性别的儿童抚养长大的经历,难以通过想象和主观观察得出。即使功利地讲,出于 Pass 的需要而与顺性别女权主义者朋友交流总是能获得更多的东西。我们将会在之后的部分详细讲讲这两点。
在进行接下来的讨论前,我们至少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女性,无论是作为拥有该性别的人群,还是作为女性刻板印象的气质,都一直出于被压制、压迫、扼杀的地位。虽然我并不希望读者是另类右翼者,但是出于当下全球互联网都在被极右思想冲击,我不得不对此做出澄清:女性并没有像某些人所说一样已经处于“高等性别”的地位;恰恰相反,是因为女性长期在新闻等方面失权,而在舆论上被迫被污名化为只要特权等形容词。
如果你不相信这一点(我很遗憾、并且对你基本的观察力很失望),请反过来思考(如果你是一个跨性别者) 跨性别是否像这些人所说的一样是特权群体?当别人说,“真正的跨性别应该” balaba 而“美国已经被白左跨性别控制,有 97 种性别” 的时候,你怎么想?
那么,对于 “真正的女权主义者是承担责任的,虚假的女权主义者只要义务”,“公检法已经被女权控制” 等右翼男权狗哨,希望你看看生活中的事实,重新想一想,真相是什么。
女性被压迫的事实
性别选择性堕胎:中国的性别选择性堕胎现象非常严重,引用维基百科引用官方数据如下:
2014年中国大陆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5.88:100 [28],2015年为113.51:100,2016年为112.88:100,2017年为111.9:100 [29]。中国大陆的性别比长期不均衡,至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男性比例上升至51.24%
请注意该数据, 以 102 :100 为正常数据,115.88 意味着每本应出生 100 个女婴时,平均有 11.97 个女婴被杀死。这意味着约 12% 女婴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出生的权力。这是选择性的性别屠杀。如果你对这个数字没有概念——请想象一下你的学校。假设一个班上有 25 个男生,你需要选择 3 个人杀掉,才能恢复正常的性别比。请问你应该杀掉哪 3 个人? 性别比即为没有任何争议的女性面临的被系统性厌恶的铁证。
女性气质会让你遭到可能产生生命危险的社会恶意:【女摩友为什么少?因为容易被别车!】 女摩友为什么少?因为容易被别车!_哔哩哔哩_bilibili ,UP 主“百万骑行装备” 给粉丝发女装福利,人生第一次遇到如此高频率的别车。事实证明,如果你被人认为可能是“好欺负”的女生,可能会被恶意插队、故意划损、甚至故意碰撞。
看到这个视频突然想到我家今年新买了一辆粉色的电动车,是我爸挑的,结果买回来没几天被划了两次,而且都是好好停着被划的。之前都没联想到有性别特征的原因,看了这个视频醍醐灌顶,问我爸以前的电动车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他说从来没有,我服了。 —— 评论区
劳动分工与“隐形劳役”: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与多国学者研究,全球范围内的无偿照护劳动(育儿、做饭、洗衣、照顾老人)有超过 75% 是由女性承担。在中国这一比例甚至更高,尤其在农村或城乡接合部地区,女性几乎承担了全部家务劳动与子女教养责任,却常被视为“理所应当”。这是一种经济不可见的剥削:她们的劳动不被计算入GDP,不获得报酬,不享有休息权,甚至被合理化为理所当然,例如被认为“女性更爱干净”,而“家务总是最先忍受不了的那个人做的”。
坏男人,好男人
请注意,上面的事实有一个特点:它并不受“你”的控制。你不需要成为一个“坏男人”才能压迫女性,实际上可能一个男孩的出生就是踩着他姐姐的尸骨而出生的。你也无法因为自己是一个“好男人”就能脱离压迫制度,社会会强制性地把从女性那里剥夺来的利益塞给你,例如一个“好男人”的母亲可能因为系统压迫无法获得能力匹配的工作,不得不花更多时间在孩子身上,才培养出“好男人”。这就是为什么 Not All Men (“不是所有男人都这样”)常常会被视为偷换议题焦点、消解女性的发声权利的一种表现。并不是所有男人都直接施暴,但“并非所有男人”从来不是重点,重点在于:在结构性、系统性的压迫下,你没有办法置身事外。
“Not All Men” 的逻辑等同于“并不是所有流浪狗都会咬人”,可为什么人们依然在看到流浪狗时下意识避开?因为个体的例外无法改变群体的事实。女性并不是因为“误会”男人才感到不安全。是因为太多的女性亲身经历了、或者认识的人经历了真实的暴力、骚扰、羞辱、压迫。是因为她们所处的社会结构要求她们如此生存,否则她们要为此付出代价。这种普遍的恐惧感不是“某一个坏男人”造成的,也不是“某一个好男人”可以疗愈的,而是系统性暴力的直接产物。
另类右翼、新男权与非自愿独身者,“逆向歧视”
在当代网络文化出现了一系列高度性别化的反动意识形态群体,其中尤以“另类右翼”(Alternative Right)、“新男权主义者”(Men’s Rights Activists, MRAs)与“非自愿独身者”(Involuntary Celibates, 简称Incel)最具代表性。这些群体皆共同体现了对女性与性别解放进程的结构性敌意,并借助网络媒介,以笑话、meme、叛逆的意见领袖、“说出真相者” 等多种形式形塑出一套具有高度感染力的厌女话语体系。这些话语不仅在网络空间中广泛流传,更在现实中产生了对公共舆论与性别正义构成实质性威胁。
“另类右翼”最初是由美国极右理论家 Richard Spencer 在2008年左右提出的概念,旨在区隔于传统保守主义的、更加激进与“数字化”的民族主义运动。该思潮强调白人身份的优越性,反对多元文化、性别平权与LGBTQ+权利,主张恢复所谓“传统的西方文明价值”。另类右翼者认为,“白人文化”在多元文化中被边缘化,社会上存在“逆向歧视”,认为女性、少数族群、跨性别等群体“实际上是特权群体”并且获得了“不公平的优待”。另类右翼话语通过讽刺、模因、政治不正确言论等形式,在 Reddit、4chan、Twitter 等平台迅速扩散,吸引了大量年轻男性的追随。
新男权主义者群体则更专注于性别领域内部的“反抗”。这类群体通常自我定位为“理性维权者”,宣称在现代社会中,男性因法律、媒体、教育等制度性机制而被边缘化。他们强调父权权力已被解构殆尽,而女权运动则“过度扩张”至对男性的压迫,其话语中常见“男性自杀率高”、“男性在离婚和子女抚养中遭遇司法不公”等主张。与另类右翼类似,他们也主张女权主义在对男性进行“逆向歧视”。新男权主义者觉得男性才是弱势群体,女性可以随意的诬告男性强奸,毁掉任何一个男性的人生。新男权主义者通常把 “性需求” 当成是基本人权,并且认为女性不和他们做爱是故意哄抬逼价、制造婚恋关系上的供需不平等。
“非自愿独身者”(Incel)群体则完全撕破脸皮,是性别结构焦虑在网络亚文化中的极端化表达。Incel 原是指那些希望拥有恋爱或性关系却长期无法达成的个体,最初以互助社群的形式出现,然自2010年代后期起,其社群迅速激进化,演变为带有强烈暴力、厌女与阴谋论色彩的网络次文化。Incel话语构建了一整套二元论世界观:在其中,部分“高贵的”、“特权的”、拥有性资源的男性,与被认为享有性选择权、可以随意选择谁来做爱的的女性成为仇恨投射的对象,而普通男性则被描绘为无力挣脱的“性别底层”,他们相信外貌决定一切,认为女性只择优而弃弱,性资源在自由市场化的过程中被极度垄断。
我一直在加粗“逆向歧视”这个词语。实际上,仔细想想就会意识到逆向歧视有多么荒谬:如果说 “工人在逆向歧视资本家,其实工人才是真正的特权群体,因为工人可以随便骂资本家,但是资本家却不能拿工人怎么样”, 大多数人都会立刻意识到不对:歧视与否需要看两个群体的权力关系而不是单看表现形式。
将 “女人可以骂男人” “女人拥有彩礼的议价权” “全女法庭不公平” “女人不需要搬水、工作如果有男人杂活就会要男人承担” 等等故意曲解为 “女性拥有更大权力”,正是这些右翼话语惯用的偷换概念伎俩。这种论述方式通过抽离真实的社会结构与历史脉络,只关注形式上的表观,把原本处于系统性压迫地位的群体,包装成“特权者”或“既得利益者”。在这种叙事下,女性的愤怒被视为“反向歧视”,而男性的支配与暴力则被美化为“合理反抗”。这就是父权制一直在干的事情:将弱势者置为一个“有错”的境地,极度放大弱势者的应激反应,合理化强权者的欺凌和压迫。
- “女人可以骂男人”——是的,但是男人一直都在习惯性的骂女人,远比女性的反击多得多得多。检查一下国骂就会发现,无论是 “操你妈” 还是 “傻逼” “婊子” 等等,无一不是男性一直在习惯性骂女人的表现。在这样的环境下,男权者怎么好意思说女人可以骂男人?
- “女人拥有彩礼的议价权”——但是他们故意忽略了彩礼是给父母而不是给一直不受宠的女儿的。何况,从根本上,为什么会有这么高彩礼?这是堕女婴的直接下场。男性比例高达 51.24%,抛开同性恋等不谈,意味着大约 2.48% 的男性永远不可能在一夫一妻制度下结婚:总共都没那么多活着的女人。这意味着婚恋市场一定是困难到 2.48% 的男性无论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找到对象。表现在经济上,便是彩礼;表现在情感上,就是更高的道德要求。
- “全女法庭不公平”——但是在女人有资格从政前,法庭一直是全男的。著名的南京彭宇案,法官不也是男的吗?但如果是女人当法官,人们就会觉得这是女人的问题;男人当法官,人们觉得这是法官个人的问题。这体现的显然是赤裸裸的厌女逻辑。女人一旦上桌,任何问题都是女人上桌造成的,这便是这些人的真实想法。
- “女人不需要搬水、工作如果有男人杂活就会要男人承担”——这也是小男孩最常见的想法了。但是,大男子主义难道是女人想出来的吗?稍微想想就知道,是父权制一直试图把女人描述为“柔弱无力”“需要保护”“依附男人”的形象,男人才被迫成为“被依附”的对象,承担了更多责任。
事实上,不仅是女性受害,实际上所有的弱势群体都在被受害。当跨性别被加上 “沃尔玛购物袋” “武装直升机” “白左的阴谋” “过度的政治正确” 这样的印象的时候,对跨性别的欺凌和侮辱就被包装为“维护性别正义的”符合道德的行为。即使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在中国跨性别只能受到更多歧视、没有任何特殊地位,右翼话语却借着想象中的“美国跨性别已经成为特权阶级了”这一稻草人,得以肆无忌惮地对现实中的、正在遭受不公对待的跨儿们进行“正义的辱骂”。这在逻辑上是完全一致的。
连动物也会受到这样的污名化。例如虐猫文化在中国互联网的流行,猫被指责是“生态杀手”“入侵物种”(哪怕实际上猫早就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并不是入侵了城市生态系统,而对物种的毁灭性打击,人类比猫多上万倍)。对猫的一点点关爱,会被污名化为“极端爱猫人士”、“把猫看得比人更重要”。猫在遇到体形比它大许多倍的人的时候产生的应激反应也被无限放大,因此虐猫者得以合理化自己“反击”动物的行为。——哪怕事实上所有人都会承认,猫在人面前是绝对的弱小,很容易被杀死。虐猫者却通过指责猫的过错,反过来将自己立为一个被猫欺凌,才声张正义的的形象。
因此,我会说:厌女-厌性少数-厌猫 三个看似毫无关联的词语内在共享根本上一样的逻辑。女权主义并不只是在解放女性,也是在解放所有人。
男性没有被压迫吗
一些人可能会觉得,“好吧,我承认男性确实处在压迫的地位,但是男性个体不是一样的被压迫吗?那么为什么我要支持女性主义?”
男性没有被压迫吗?显而易见,答案是否;但是与新男权主义者的主张恰恰相反,男性被压迫的根源正是父权文化本身。因为父权需要贬低、打压女性来榨取来自女性的免费的劳动力。在这一方面,为了划分男与女的不同,必然产生了对男性的约束——而这种约束终究是为压迫女性服务的。男性的性别困境一旦抛开自己造成的大男子主义就根本不存在。
男同性恋经常作为被侮辱欺凌的对象。这难道是女性主义造成的吗?当然不是。上野千鹤子 《厌女》中有一些话非常的形象
被插入、被得到、成为性的客体,这些说法的另一种表达,就是“被女性化(feminize)”。男人最恐惧的,就是“被女性化”,即性的主体地位的失落。
男人的同性社会性欲望的纽带,就是相互认可的性的主体者之间的纽带。“你这家伙还真行”的赞许,便是这种主体成员之间的相互认可,也就是“好!让你加入男人世界里来”的盟约。在这个由主体成员构成的世界里,如果出现了同性恋欲望,就可能相互沦为性的客体。主体成员的客体化现象一旦发生,结果将会引发“阶层的混淆”。所以,可能导致性的主体者之间相互客体化的性爱欲望,是危险的,必须被禁忌、压抑和排除。
塞吉维克还指出,由于同性社会性欲望和同性恋欲望本来难以区别,所以对同性恋的排除便更加残酷。要否定自身本来有的东西,比起排除完全异质的东西,其行为不得不更为激烈。正因为如此,“那家伙是个同性恋”,就意味着丧失在男性集团中的成员资格,成为男人之间最大的辱骂。将不具有男人价值的男人从男人集团中驱逐出去时,使用的表达为“同性恋”,即“像女人的男人”,这个女性化的比喻,极具象征意义。男人对潜伏在自己集团中的“同性恋”的恐惧,也就是对自己也许会被当作性的客体即丧失主体地位的恐惧。所以,男性集团中对同性恋的搜索非常严厉。这就是“同性恋憎恶”(恐同)。为保证男人集团的同质性,即保证每个成员皆为性的主体,这是必不可少的。
正是男人自己把自己锁在了有毒的男子气概中。男性为了排除女性,必然需要证明自己不是女性;而这就让男人丧失了任何可能被看作女性化的行为自由。——无论这种行为是“娇弱”还是“感伤”甚至是“被爱”。因为男人需要证明自己是“男人”而不是“女人”,只要是被认为女性经常做的事情,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男人都必须远远地与此划清界限,最终成为“只有女性才能做的事情”。男人造出了毒药,并毒死了自己。
男人为成为男人而实践的同化与排除行为,不是单独一人能完成的。社会学学者佐藤裕在《论歧视》一书中尖锐地指出,“歧视需要三个人”。他的关于歧视的定义,可以稍加修改为:歧视就是通过将一个人他者化而与共同行动的另一人同化的行为。如果把前面的“一个人”换为“女人”、后面的“另一人”换为“男人”,直接就成为对“性歧视”的定义。
佐藤举出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事例。比如,男人A说,“女人脑子里怎么想的,真是弄不懂。”这句话,不是男人A对女人B说的,而是对男人C说的。男人A发出这种话语的意图,是想寻求男人C的同意,试图和他一起将女人B他者化,从而构成“我们男人”的集体认同。女人B这时是否在场无关紧要。正如佐藤指出的,排除是一种共同行为。如果男人C回答,“对,完全如此。”对男人A表示赞同(即与男人A同化),那么,歧视行为就得以完成。而假如男人C表示反对,“不,没那回事儿。”男人A的男性集体身份认同的企图就在这里失败了。那么,男人A为掩盖自己的困惑恼怒,会转而攻击男人C从男人世界的偏离,“怎么?你还是个男人吗?”不是男人就是女人,不是女人就是男人。在不允许中间项存在的顽固的性别二元制之下,偏离了男人世界,便等同与“被女性化了的男人”。
于是,我们得知,担保一个男人为男人的,不是异性的女人,而是同性的男人。男人的性的主体化,需要的是认可自己为男人的男性集团。正如拉康一语道破,“欲望乃他者之欲”,男人是通过模仿其他男人的性欲望而成为性的主体的。所以,成为男人的途径,没有任何多样性。下流话成为一种—固定格式,绝不可能成为第一人称“我”的话语,理由就在这里。男人那么拘泥于勃起能力和射精次数,是因为只有那才是男人之间可以比较的一元化尺度。当我们叹息“男人的性多么贫瘠”的时候,我们必须追溯到更为根源的问题,即,男人的性的主体化途径本身,就是一种排除了偏离和多样性的固定格式。
厌跨女症:厌女文化直接影响跨女
尽管所有跨性别者都可能因违反性别规范而遭遇污名化和歧视,但跨性别女性通常面临比跨性别男性更集中、也更恶意的社会妖魔化。
媒体通常会对跨性别女性外貌和身体进行猎奇式的渲染,同时对她们动机进行性化——例如,她们往往被描述为以讨好男性为卖点的性工作者, 如“泰国人妖表演”;或者在 TERF 眼中被指控是“为了进入女澡堂”而“假装成女人”的“性变态”男性。即使在表面上 “中立”的报道中,跨性别女性也是最常被提起的“问题”,例如跨性别者应不应该参加运动会的问题,没有人在意合法使用睾酮(属于兴奋剂的一种)的跨性别男性如果不应该去男子组会不会有真正的不公平优势,反而对压制睾酮的跨女运动员大肆报道,仿佛跨女运动员已经证据确凿地偷窃了女运动员的奖励。
相比之下,跨性别男性虽然也面临媒体误解和边缘化,但很少被同样的性化、猎奇化描述。他们的跨性别行为往往被 TERF 解释为“不懂事的女孩追求男性特权”或“出于厌女而试图逃离女性这一性别”,而不是源于危险或变态的性欲。
其实这很好理解。因为整个社会被浸透在厌女中,而在厌女文化的叙事中,男性-女性是阶级分明的,“成为男性”被默认为是一种“向上移动”的行为,是可以被接受的,甚至是可以被赞扬的。花木兰替父从军,“安能辨我是雌雄”,被加入中学课文;梁山伯与祝英台,祝英台因为女子不能在外抛头露面,于是乔装成男子,没有任何人觉得这不妥,反而是传为一段佳话。反之,“成为女性”则被视为“危险的”、“向下的”、甘愿放弃性别权力的可疑行为。社会潜在地认为,成为女性是不明智的,如果一个“男性”希望“成为女性”,那么人们会怀疑它一定是想要通过放弃手头的权力获得更大的权力,例如“可以自由的看女澡堂”。
这并不是说跨男不会受到恐跨的影响;社会的总体看法和落在个人上的压力有很大的区别。然而,无可否认的是,跨女的确更加受到社会猎奇的视线关注。
这种不对称的结构揭示出一个事实:针对跨性别男性和女性的区别对待,即使同样属于遭到歧视偏见,内在亦有差别。跨性别女性受到歧视并不只在于她们违反了不应打破的性别规范,还在于她们跨向了 “女性”这一性别。 因此,跨性别女性人群的边缘化 不仅仅是恐跨(Transphobia)的结果,更确切地说,应该将这种现象描述为厌跨女症 (Transmisogyny)。 正因如此,跨性别女性才总是受到更多的关注和讨伐,因为这社会总是习惯性地把“类女性者”摆在一个被凝视被观赏的地位。
Whipping Girl 与 SCUM
Julia Serano 2007 年出版的《Whipping Girl》(不知道中文译名)[2:1] 中发明了 Transmisogyny 即厌跨女症这个词。厌跨女症这个词随即成为跨性别女性主义(transfeminism)的焦点,并且在交叉女权主义中经常被引用[3]。
女权主义者长期以来所说的“性别歧视”实际上由两种力量组成。一种是“传统性别歧视”,即认为女性和女性气质比不过男性和男性气质,或者不够合法。但为了维持这种等级制度,还需要有一种方法来阻止人们模糊或穿越这些区别。我将这种力量称为“对立性别歧视”,并将其定义为“认为女性和男性是僵化的、相互排斥的类别,每个类别都拥有一套独特且不重叠的属性、能力、能力和欲望”。换句话说,跨性别恐惧症(以及恐同症)源于对立的性别歧视。—— What Is Transmisogyny?. My 2007 book Whipping Girl is probably… | by Julia Serano | Medium
显然,这种说法和《厌女》中提到的“男人最恐惧的,就是被女性化,即性的主体地位的失落” 是相吻合的。也就是说,对跨女的羞辱并不是“和女权主义无关”的额外偏见,而正是厌女症的极端形式。跨女主动选择了一个被男性共同体所贬低的位置,并因此被视作背叛了男性特权的“叛徒”。这种叛逆不仅威胁了二元性别制度的稳定,也动摇了男性主体性的幻想地位。男性将不得不面对一种可能性,即自己有可能失去自己构造的男性身份。因此,厌跨女症不仅仅是跨性别恐惧症的一种,更是父权制如何维持性别秩序的关键机制之一:它既惩罚那些“想成为女人”的人,也警告所有“已经是女人”的人——不要太像她们,不要越界,否则你也会被同样的方式羞辱与惩罚。
从这个意义上讲,跨女并不是女性主义的局外人,而是那种最彻底、最极端地被女性化、并因此而遭遇羞辱的主体。或者说当我们说出“女性是一种处境”的时候,无论如何,跨女都是属于这份处境的。她们的存在揭示出:男人们厌恶女性气质并不是因为女性气质刻板印象如今包含了温柔、顺从等“软弱”的、“向下”的东西,相反的是,是因为需要一个被维护的男性气质,才发明了被厌恶女性气质。女性气质而是一个被系统性惩罚的符号集合。而跨女所遭遇的羞辱,不是因为她们“模仿”了女性,而是因为这个社会从来都无法忍受和不敢正视“成为女性”的选择。这不仅击穿了“天生如此”的性别本质主义,也撼动了男性身份的合法性建构。
事实上,多种女性主义流派,甚至包括激进女性主义,都有类似的描述:
男性完全以自我为中心,无法交流、同情或认同,又充斥着无处不在四处弥漫的大量性欲,他们在心理上是被动的。但男性讨厌被动,所以他们将其投射到女性身上,把男性的插入行为定义为主动,以此证明他行(“证明他是男人”)。而证明这一点的主要方法是去插逼(大屌男人操牛逼)。由于所试图证明的观点本身就是错误的,男性必须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它。因此,做爱是一种令人绝望的强迫行为,男性试图证明他们不是被动的,证明他们不是女人;但他们本身就是被动的,并且的确想成为女性。
……
父性对男性的影响,具体地讲,使他们成为“男人”,其实就是高度抑制他们所有被动性、与同性相恋和渴望成为女性的冲动。每个男孩都想模仿他的母亲,成为她,被她同化,但爸爸禁止这样做;爸爸也想成为母亲;爸爸想被母亲同化。所以爸爸时而直接时而间接地告诉男孩,不要成为娘娘腔,要像一个“男人”。男孩害怕被嘲笑,“尊重”他的父亲,顺从,变得像爸爸一样,“男性”的模范,全美国的理想型——举止得体的异性恋者。
—— 索拉娜丝 《SCUM 宣言》
大部分的女性主义,只要不是 so-called 激女,都是对“对立性别歧视”的颠覆。甚至包括激进女性主义者本身。SCUM 宣言中还包括一种非常……神奇的论述:
如果男性足够明智的话,他们便会寻求真正成为女性,他们会进行深入的生物研究,通过对大脑和神经系统的手术,使男性在心灵和身体上都能够转化为女性。
我很喜欢 Andrea Long Chu 在 On liking women 中对这句话的看法:“男性到女性的性别过渡(transition)可能表达的不仅仅是对男性身份的不认同(disidentification),还包括从男性群体中的脱离(disaffiliation)。在这里,过渡就像革命一样,在审美层面上被重新构想,好像跨性别女性决定进行过渡,不是为了「确认」某种固有的性别认同,而是因为当男性是愚蠢和无聊的。”
由于是没写完的长文,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了。